卡夫卡(Franz Kafka)与存在主义文学的关系,始终是20世纪文学批评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。尽管他生前未公开宣称哲学立场,且其作品创作时间早于存在主义文学流派的正式形成,但《审判》《城堡》《变形记》等文本中呈现的荒诞体验、个体困境与存在追问,使其被后世广泛视为存在主义文学的先驱。这种判断并非基于时间先后的简单对应,而是源于其创作特质与存在主义哲学内核的深刻共鸣。
一、创作特质的“存在主义式”表达
1. 荒诞情境的构建:对现代性困境的寓言化呈现
卡夫卡的作品以“日常中的非日常”为核心叙事策略,将荒诞性植入现实逻辑的缝隙中。《审判》中,主人公约瑟夫·K在30岁生日当天被“法院”逮捕,却无人告知罪名,甚至无法确认逮捕者的身份。他穿梭于法庭、银行、妓院等现实场景,却始终被困在无解的司法迷宫中,最终被处决于采石场。这种“无罪之罪”的悖谬,恰如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——个体被抛入一个无意义、无逻辑的世界,所有挣扎都沦为徒劳。
《城堡》则将荒诞性推向极致:土地测量员K历经跋涉抵达城堡管辖的村庄,却始终无法进入象征权威的城堡。他与官员、村民的对话充满循环论证,如“城堡会通知你”“但城堡从未通知我”“那是因为你不该知道”……这种语言游戏消解了沟通的可能性,暗示现代官僚体系对个体的异化与吞噬。卡夫卡通过这种“有目的的无目的性”叙事,揭示了存在主义的核心命题:世界是荒诞的,而人必须在荒诞中寻找意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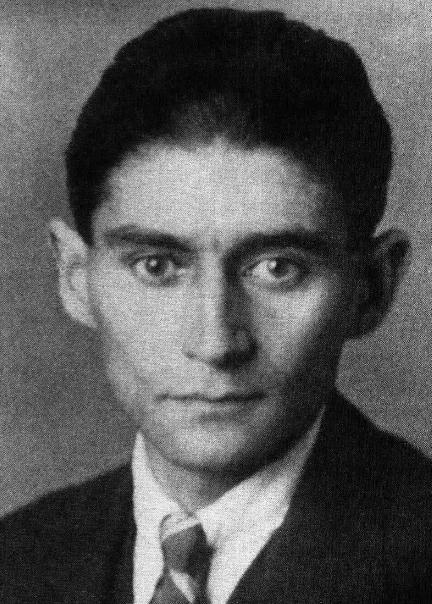
2. 孤独个体的困境:从“自我”到“非人”的异化
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往往是符号化的“K”或“格里高尔”,这种去个性化命名本身即暗示个体的普遍性困境。《变形记》中,推销员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甲虫,失去语言能力与人类形态后,他逐渐被家庭排斥:父亲用苹果砸他,母亲惊恐晕厥,妹妹从最初的照料者变为最终提议“清除”他的人。格里高尔的异化不仅是生理的,更是社会关系的彻底崩塌——他从“家庭经济支柱”沦为“需要处理的垃圾”,映射出现代社会中人的物化与工具化。
这种异化体验与存在主义对“他人即地狱”的阐释形成互文。萨特在《密室》中通过“地狱是他人”的台词,揭示人际关系中的压迫性;而卡夫卡则通过格里高尔的死亡(“他的头无力地耷拉下来,鼻孔里最后喷出一丝微弱的气息”)完成对存在本质的叩问:当个体失去社会认同,其存在是否还具有价值?
3. 黑色幽默的叙事:在绝望中保持冷静的审视
卡夫卡的语言风格以“冷峻客观”著称,他常用法律文书般的朴实文风叙述最荒诞的事件,形成强烈的反讽效果。《审判》中,K被捕后仍需正常上班,甚至在法庭上与律师讨论案件时,还能冷静分析“法院的腐败是系统性的”;《城堡》中,K与助手们围坐在桌前讨论如何进入城堡,却始终无人行动,对话沦为无意义的重复。这种“日常化”的叙事态度,将悲剧内核包裹在喜剧外壳中,恰如黑色幽默的精髓——以笑的方式哭,以荒诞的方式真实。
这种风格与后世存在主义作家的创作形成呼应。例如,贝克特《等待戈多》中,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日复一日等待“戈多”,却始终不知其为何人、何时来,他们的对话充满自相矛盾与逻辑断裂,却以极简的舞台动作传递出存在的虚无感。卡夫卡虽未直接参与存在主义运动,但其对荒诞的审美化处理,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范式参考。
二、哲学内核的“存在主义式”共鸣
1. 对“存在”的追问:从“被抛”到“自由选择”
存在主义的核心命题是“存在先于本质”,即人首先存在,随后通过自由选择定义自身。卡夫卡的作品虽未明确使用这一术语,却通过主人公的困境呈现了类似的哲学思考。《审判》中,K的“罪”是先验的、无法证明的,他被迫在无意义的司法程序中挣扎,这种“被抛入世界”的体验,与海德格尔“被抛状态”(Geworfenheit)的描述高度契合——个体无法选择出生、时代或社会角色,却必须承担存在的责任。
然而,卡夫卡并未止步于“被抛”的无奈。在《城堡》中,K尽管始终无法进入城堡,却从未放弃争取:他贿赂官员、伪造文件、与村民周旋,甚至在临终前仍等待“允许居住”的通知。这种“徒劳的坚持”暗含存在主义的另一重命题:自由选择本身即意义。即使结果注定失败,个体仍需通过行动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,正如萨特所言:“人是被判定自由的,因为我们一无所靠,只能依靠自己。”
2. 对“权力”的批判:从“城堡”到“全景敞视监狱”
卡夫卡对官僚体系的描绘,与存在主义对权力结构的批判形成深刻对话。《城堡》中的城堡是抽象权力的象征,它通过文件、信使、官员等符号系统维持统治,却始终拒绝与个体直接对话。K的困境揭示了现代权力的本质:权力不再依赖于暴力,而是通过规则、程序与话语构建“真理体制”。这种批判与福柯的“全景敞视监狱”理论不谋而合——权力通过监视、分类与规范化,将个体驯化为自我规训的主体。
存在主义作家如加缪,在《鼠疫》中通过里厄医生的抗争,提出“反抗荒诞”的伦理选择;而卡夫卡则选择以“沉默的抵抗”呈现对权力的批判。《审判》结尾,K被处决时“像一条狗一样死去”,这一画面既是对司法暴力的控诉,也是对个体尊严的坚守——即使死亡,也要以“人”的姿态而非“狗”的姿态存在。
3. 对“信仰”的悬置:从“上帝已死”到“等待戈多”
存在主义诞生于宗教信仰崩塌的时代背景之下,尼采“上帝已死”的宣言标志着传统价值体系的解体。卡夫卡的作品虽未直接讨论宗教,却通过“信仰的缺失”传递出类似的危机感。《城堡》中,K试图通过进入城堡获得“合法性”,但城堡始终拒绝给予明确答复,这种“悬而未决”的状态暗示了现代人面对终极问题的无力感——当上帝缺席,人如何寻找存在的依据?
这种困境在存在主义文学中得到延续。贝克特《等待戈多》中,“戈多”始终未现身,象征着传统信仰的失效;而卡夫卡《乡村医生》中,医生冒着暴风雪出诊,却发现病人“健康得令人绝望”,这一悖谬场景同样揭示了现代医疗(乃至现代科学)无法解决存在焦虑的局限。卡夫卡虽未提供答案,却通过文本的开放性,迫使读者直面自身的存在困境。
三、历史语境中的定位:先驱者与同路人
1. 时间错位:先于流派的创作实践
存在主义文学流派正式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法国,以萨特《恶心》(1938)、加缪《局外人》(1942)为标志;而卡夫卡的主要作品创作于1912—1924年间,且大部分在其去世后(1925—1927)才由好友马克斯·布洛德整理出版。这种时间上的错位,使得卡夫卡无法被纳入存在主义文学的“同时代者”范畴。
然而,文学流派的界定从来不仅依赖于时间,更取决于精神内核的共鸣。卡夫卡对荒诞、异化与存在追问的探索,与存在主义哲学形成跨时空的对话。正如保罗·利科所言:“卡夫卡介于尼采和存在主义各家之间,他描绘出海德格尔《存在与时间》中的人被‘抛入’世界,萨特的无神世界,以及加缪的荒谬世界。”这种评价肯定了卡夫卡作为存在主义“精神先驱”的地位。
2. 哲学影响:从克尔凯郭尔到海德格尔
卡夫卡的思想资源虽未直接来源于存在主义哲学,却与存在主义的先驱者存在深刻关联。其日记中多次引用克尔凯郭尔的箴言,如“对死亡的渴望是萌生认识的第一个征兆”,暗示了对存在本质的思考;而他对官僚体系的批判,则与马克斯·韦伯的“理性化铁笼”理论形成互文——现代社会的“去魅”过程,既带来了效率,也导致了意义的丧失。
海德格尔对卡夫卡的解读更具启示性。他在《林中路》中提及《城堡》时,将K的困境解读为“此在”(Dasein)在“常人”(Das Man)世界中的沉沦与觉醒。K对城堡的执着,恰如海德格尔笔下的“向死而生”——唯有通过直面存在的终极界限(死亡),个体才能从“沉沦”中觉醒,获得本真的存在状态。这种解读虽非卡夫卡本意,却揭示了其文本的哲学深度。
3. 文学传承:从卡夫卡到后现代主义
卡夫卡的影响远超存在主义文学范畴,其创作特质为20世纪下半叶的荒诞派戏剧、黑色幽默小说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重要范式。贝克特《等待戈多》中“无意义的等待”、尤内斯库《秃头歌女》中“荒诞的对话”、品钦《万有引力之虹》中“熵增的宇宙”,均可见卡夫卡式荒诞的影子。
这种传承不仅体现在主题上,更在于叙事策略的创新。卡夫卡通过“去情节化”“去个性化”“语言悖谬”等手法,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框架,为现代文学开辟了新的可能性。正如奥登所言:“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,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。”这种“困境”的普遍性,使其作品超越了时代与流派的界限,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