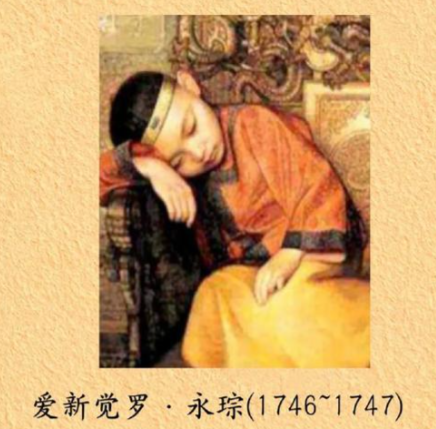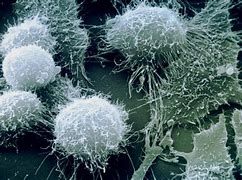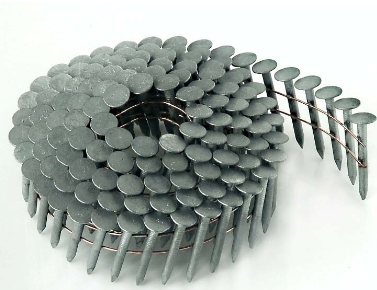阿蒂尔·兰波,十九世纪末法国著名象征派诗人,出生于1854年法国阿登省夏尔城,1891年逝世,代表作品长诗《地狱中的一季》。
个人简介
让·尼古拉·阿尔蒂尔·兰波(法语: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,1854年10月20日-1891年11月10日),或译阿尔图尔·兰波、韩波、林包德,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。兰波是无法被归类的天才诗人,创作时期仅在14-19岁,之后便停笔不作。他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影响,是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鼻祖。

阿蒂尔·兰波
人物生平
青年时期
兰波出生于法国东北部夏尔维勒乡村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。少年时代的兰波是一个好动而才华横溢的学生。15岁那年,他就能以拉丁文写作各种诗歌并因此赢得了很多奖赏。
1870年,兰波的老师乔治·伊森巴尔成为兰波在文学道路上的领路人。在他的指导下,兰波开始用法语写诗,其法语诗歌的创作水平进展迅速。兰波性格叛逆,屡次离家出走,甚至曾经参与过1871年的巴黎公社组织。他在诗歌《巴黎人的狂欢或巴黎的重生》一诗中描述了自己参与巴黎公社的这段经历。1871年以后,兰波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,他开始酗酒,并经常蓄长发、衣衫褴褛的招摇过市,以图嘲笑那些一本正经的中产阶级。他给他的老师伊森巴尔写信,系统阐述他的诗歌创作理论,即在“漫长的、庞大的、理性的骚乱中”加入幻觉的因素。
1871年9月底,兰波再次回到巴黎,不过这次是应著名象征主义诗人保尔·魏尔伦的邀请。魏尔伦曾读过兰波的著名作品《醉舟》,十分爱慕兰波的诗才。来到巴黎之后,兰波住在魏尔伦的家里。很快,魏尔伦便和这个17岁的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坠入爱河,他们成为巴黎诗坛著名的同性情侣。两人同居之后,生活挥霍而放任,酗酒和吸食大麻是家常便饭。他们为巴黎的文学精英团体所不容,而兰波的恃才傲物更是引起许多的反感。这一时期,兰波创作了大量具有震撼力的诗作,他的诗歌成就甚至超过了象征主义文学的先驱波德莱尔。
兰波和魏尔伦之间的同性恋情日益炽烈。1872年,魏尔伦甚至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,和兰波一同私奔至伦敦。1873年7月,两人在布鲁塞尔火车站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吵,随后魏尔伦用枪打伤了兰波的手腕,一气之下兰波叫来警察,魏尔伦被逮捕。被捕期间,魏尔伦甚至被迫接收了一系列具有侮辱性的心理治疗,原因是魏尔伦的妻子指控她的丈夫和兰波之间不正常的“友情”。开庭审理时,尽管兰波一再宣称自己撤回对魏尔伦的控诉,法官还是判魏尔伦入狱两年。魏尔伦入狱后,兰波只身一人回到故乡夏尔维勒,在极度伤心中完成了一生最杰出的诗作《地狱一季》。这部作品是象征主义文学的精品。在诗中,兰波追忆他和魏尔伦共同生活的“地狱情侣”的岁月。他甚至以“悲伤的兄弟”、“疯癫的童贞女”来称呼魏尔伦,而自己则是他的“下地狱的丈夫”。1874年,兰波和诗人杰曼·努沃再次返回伦敦,并出版了他倍受争议的作品《彩画集》,其中包含了两首最早的以自由诗体写成的法语诗歌。
漂泊生活
1875年,兰波和魏尔伦最后一次在德国相遇。此时的魏尔伦已经获释,并被迫皈依了天主教。这个时候,兰波已经受够了早年的放纵生活,基本放弃了写作生涯,而是开始从事一些能够给他带来稳定收入的工作。
1876年夏天,他甚至加入了荷兰的军队,只是为了免费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去旅行。然而到了爪哇之后,他很快就厌倦了,并立即乘船返回法国。他曾游历塞浦路斯并最终在亚丁定居,并成为巴尔代公司的一名雇员。在这段时间,他没有再和男性产生同性恋情,而是和很多当地的女性相恋。
1877年,兰波开始徒步在欧洲大陆旅行。
1884年,兰波辞去工作,开始独立在阿比西尼亚(今天的埃塞俄比亚)经商。他从事军火走私生意,并赚了不少钱。而在这个时候,兰波的右膝盖患上滑膜炎,并很快恶化为癌症。日益恶劣的病情迫使兰波于1891年5月9日返回法国。5月27日,兰波做了右腿的截肢手术,然而这还是没能抑制癌细胞的扩散。同年11月10日,兰波在法国马赛逝世,享年37岁。
个人作品

兰波作品全集
黎明
我吻抱夏晨的黎明。
宫殿前的一切依然静寂,流水止息。绿荫尚未在林路中消失,我走过,唤醒一阵阵生动而温馨的气息,宝石般的睛瞳睁开,轻翅无声地飞起。
第一个相遇,在晨曦洒落的幽径上,一朵花告诉了我它的名字。
我朝金色的瀑布一笑,她的散发飘过松杉林:自那银白的顶端我认出了女神。
于是我一层层揭开轻纱,在小路上我挥动双臂。在平原上,我向雄鸡举告了她。
在都市里,她在教堂的钟塔与穹顶间逃匿,乞丐般飞跑在大理石的岸上。我追逐着她。
在路上,在月桂树边,我以层层轻纱将她环抱,隐约地感觉到她无限的玉体,黎明和孩子一起倒在丛中。
醒来,已是正午。
醉舟
当我顺着无情河水只有流淌,
我感到纤夫已不再控制我的航向。
吵吵嚷嚷的红种人把他们捉去,
剥光了当靶子,钉在五彩桩上。
所有这些水手的命运,我不管它,
我只装运佛兰芒小麦、英国棉花。
当纤夫们的哭叫和喧闹消散,
河水让我随意漂流,无牵无挂。
我跑了一冬,不理会潮水汹涌,
比玩的入迷的小孩还要耳聋。
只见半岛们纷纷挣脱了缆绳,
好像得意洋洋的一窝蜂。
风暴祝福我在大海上苏醒,
我舞蹈着,比瓶塞子还轻,
在海浪——死者永恒的摇床上
一连十夜,不留恋信号灯的傻眼睛。
绿水渗透了我的杉木船壳,——
清甜赛过孩子贪吃的酸苹果,
洗去了蓝的酒迹和呕吐的污迹,
冲掉了我的铁锚、我的舵。
从此,我就沉浸于大海的诗——
海呀,泡满了星星,犹如乳汁;
我饱餐青光翠色,其中有时漂过
一具惨白的、沉思而沉醉的浮尸。
这一片青蓝和荒诞、以及白日之火
辉映下的缓慢节奏,转眼被染了色——
橙红的爱的霉斑在发酵、在发苦,
比酒精更强烈,比竖琴更辽阔。
我熟悉在电光下开裂的天空,
狂浪、激流、龙卷风;我熟悉黄昏
和象一群白鸽般振奋的黎明,
我还见过人们只能幻想的奇景!
我见过夕阳,被神秘的恐怖染黑,
闪耀着长长的紫色的凝辉,
照着海浪向远方滚去的微颤,
象照着古代戏剧里的合唱队!
我梦见绿的夜,在眩目的白雪中
一个吻缓缓地涨上大海的眼睛,
闻所未闻的液汁的循环,
磷光歌唱家的黄与蓝的觉醒!
我曾一连几个月把长浪追赶,
它冲击礁石,恰象疯狂的牛圈,
怎能设想玛丽亚们光明的脚
能驯服这哮喘的海洋的嘴脸!
我撞上了不可思议的佛洛里达,
那儿豹长着人皮,豹眼混杂于奇花,
那儿虹霓绷得紧紧,象根根缰绳
套着海平面下海蓝色的群马!
我见过发酵的沼泽,那捕鱼篓——
芦苇丛中沉睡着腐烂的巨兽;
风平浪静中骤然大水倾泻,
一片远景象瀑布般注入涡流!
我见过冰川、银太阳、火炭的天色,
珍珠浪、棕色的海底的搁浅险恶莫测,
那儿扭曲的树皮发出黑色的香味,
从树上落下被臭虫啮咬的巨蛇!
我真想给孩子们看看碧浪中的剑鱼——
那些金灿灿的鱼,会唱歌的鱼;
花的泡沫祝福我无锚而漂流,
语言难以形容的清风为我添翼。
大海——环球各带的疲劳的受难者
常用它的呜咽温柔地摇我入梦,
它向我举起暗的花束,透着黄的孔,
我就象女性似的跪下,静止不动……
象一座浮岛满载金黄眼珠的鸟,
我摇晃这一船鸟粪、一船喧闹。
我航行,而从我水中的缆绳间,
浮尸们常倒退着漂进来小睡一觉!……
我是失踪的船,缠在大海的青丝里,
还是被风卷上飞鸟达不到的太虚?
不论铁甲舰或汉萨同盟的帆船,
休想把我海水灌醉的骨架钓起。
我只有荡漾,冒着烟,让紫雾导航,
我钻破淡红色的天墙,这墙上
长着太阳的苔藓、穹苍的涕泪,——
这对于真正的诗人是精美的果酱。
我奔驰,满身披着电光的月牙,
护送我这疯木板的是黑压压的海马;
当七月用棍棒把青天打垮,
一个个灼热的漏斗在空中挂!
我全身哆嗦,远隔百里就能听得
那发情的河马、咆哮的漩涡,
我永远纺织那静止的蔚蓝,
我怀念着欧罗巴古老的城垛!
我见过星星的群岛!在那里,
狂乱的天门向航行者开启:
“你是否就睡在这无底深夜里——
啊,百万金鸟?啊,未来的活力?”
可是我不再哭了!晨光如此可哀,
整个太阳都苦,整个月亮都坏。
辛辣的爱使我充满醉的昏沉,
啊,愿我龙骨断裂!愿我葬身大海!
如果我想望欧洲的水,我只想望
马路上黑而冷的小水潭,到傍晚,
一个满心悲伤的小孩蹲在水边,
放一只脆弱得像蝴蝶般的小船。
波浪啊,我浸透了你的颓丧疲惫,
再不能把运棉轮船的航迹追随,
从此不在傲慢的彩色旗下穿行,
也不在趸船可怕的眼睛下划水!
元音
A黑、E白、I红、U绿、O蓝:元音们,
有一天我要泄露你们隐秘的起源:
A,苍蝇身上的毛茸茸的黑背心,
围着恶臭嗡嗡旋转,阴暗的海湾;
E,雾气和帐幕的纯真,冰川的傲峰,
白的帝王,繁星似的小白花在微颤;
I,殷红的吐出的血,美丽的朱唇边
在怒火中或忏悔的醉态中的笑容;
U,碧海的周期和神秘的振幅,
布满牲畜的牧场的和平,那炼金术
刻在勤奋的额上皱纹中的和平;
O,至上的号角,充满奇异刺耳的音波,
天体和天使们穿越其间的静默:
噢,奥美加,她明亮的紫色的眼睛!
黄昏
夏日蓝色的黄昏里,我将走上幽径,
不顾麦茎刺肤,漫步地踏青;
感受那沁凉渗入脚心,我梦幻……
长风啊,轻拂我的头顶。
我将什么也不说,什么也不动;
无边的爱却自灵魂深处泛滥。
好像波西米亚人,我将走向大自然,
欢愉啊,恰似跟女人同在一般。
群鸦
主啊,当牧场上寒气萧森,在罗列着古老十字架的路上
当荒村中,悠长的三祷经,在沟渠上,在洼地上
在花草凋残的一会儿散开一会儿集合
原野上寂静无声
愉快的群鸦,在昔日的死者所长眠的
在广阔的天空中布阵,法兰西原野上,你们,在这冬天
成百累千地回翔盘旋
寒风袭击着你们的窝巢,使行人有无穷的感慨?
这奇美的军队发着凄厉的叫声,啊,全身丧服的乌鸦
你们沿着黄浊的江流,你们是义务的助哀人
牧神的头
在树丛这镀着金斑的绿色宝匣中,
在树丛这开着绚烂花朵的朦胧中,
睡着那甜蜜的吻,
突然,那活泼打乱一片锦绣,
惊愕的牧神抬起眼睛,
皓齿间叼着红色的花卉,
他那陈年老酒般鲜亮的嘴唇,
在树枝间发出笑声。
他逃走了——就像一只松鼠——
他的笑还在每片树叶上颤动,
一只灰雀飞来惊扰了
树林中正在沉思的金色的吻。
橱柜
这是一个雕花的大橱,阴暗的橡木,
十分古老,一副老奶奶的面孔;
橱门打开,一股陈酒与醉人的芳香,
便从阴影之中溢出来。
橱柜里装满杂乱的古董,
香香的黄手绢,女人和孩子的围兜,
枯萎的旧花边,
祖母的头巾,上面印着奇异的飞禽走兽。
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徽章,
白色、栗色的发绺,干花和肖像,
芳香混合着水果的香味。
——噢,古老的橱柜,你了解许多故事,
当乌黑的大门“吱吱”打开,
你就将那一段段往事娓娓道来。
1870年10月
清晨
我难道没有一次英勇、美好而又虚幻的青春,幸运地写在金页片上?出于怎样的疯狂、怎样的错误,现实中我才如此虚弱?你们说野兽因悲伤而抽泣,病人绝望,
死者被梦魔折磨,那么,请你们也讲讲我的沉沦与昏睡的缘由吧。我再也无法说清自己,就像乞丐无从解释他们念诵的《天主经》《圣母经》,我连话也不会说了!
不过今天,我和地狱的缘份已尽。那确曾是一座地狱;古老的地狱,人子打开了它的大门。
同样的沙漠,同样的夜,我又在银色的星辉下睁开
疲惫的双眼,而生命的主、朝拜初生耶稣的三博士,心灵与思想依然无动于衷。我们何时才能在沙滩与群峰之上,向着新的劳动、新的智慧致敬!为暴君、魔鬼的逃亡,迷信的终结而欢呼——成为最初的使者——迎接人间的圣诞!
天国之歌,人民的脚步!奴隶们,我们从不诅咒生活。
永别
已经是深秋!——何必惋惜永恒的阳光,既然我们
立誓要找到神圣之光——远远离开那死于季节嬗替的人。
秋天。我们的航船在静止的雾霭中转向苦难之港,朝着沾染了火与污秽的大空下的都城驶去,啊!衣衫槛褛,雨水浸坏的面色,喝得烂醉,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千万种情爱!这吞食无数灵魂、无数尸体的鬼女王,她决不肯就此罢休,而且亿万死去的灵魂还要接受审判!
我看见我的皮肉被污泥浊水和黑热病侵蚀蹂躏,头发、腋下生满蛆虫,心里还有大蛆虫辗转蠕动,我躺在不辨年龄,已无知觉的不相识的人中间……我也许就死在这里了……可怕的景象!我憎恨贫穷。
我怕严寒的冬日,因为那是需要安全舒适的季节!
——有时我看到一望无际的海滩上空布满洁白如雪、欢欣鼓舞的国度。一艘金色的大船,在我上空有彩旗迎风摇曳。我创造了应有尽有的节日,应有尽有的胜利,
应有尽有的戏剧。我还试图发明新的花卉,新的星辰,新的肉体,新的语言。我自信已经取得超自然的法力。
怎么!我必须把我的想象和我的记忆深深埋葬。艺术家和说故事人应得的光荣已经被剥夺!
我呀!我呀,我说我是占星术士或者天使,伦理道义一律免除,我还是带着有待于求索的义务,有待于拥抱的坎坷不平的现实,回归土地吧!农民!
我受骗了,上当了?仁慈对于我是否也是死亡的姐妹?
最后,因为我是靠谎言养育而生,我请求宽恕。好了,好了。
什么伸出友谊之手?到哪里去寻求援救?
重要作品
《诗集》
《醉舟》(1871年)
《地狱一季》(1873年)
《彩画集》(1874年)
《兰波书信集》
人物影响

天才诗人兰波
诗人兰波分成两个部分:谜一般的诗篇和丰富的人生构成的传奇。他为后来的世界确立了一种生存和反叛的范式,20世纪后“兰波族”成为专有名词,崇拜、模仿兰波的群体越来越壮大。二战结束后,作家亨利·米勒预言:在未来世界上,兰波型将取代哈姆雷特型和浮士德型,其趋势是走向更深的分裂。1968年,法国巴黎反叛学生将兰波的诗句写在革命的街垒上:“我愿成为任何人”、“要么一切,要么全无!”
兰波对现代文学、音乐和艺术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。他在巴黎的生活经历曾经于1995年被拍成电影《全蚀狂爱》,由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扮演。
兰波的创作是法语诗歌历史上的重大变革。他本人是一位无法被归类的诗人,有人认为他是象征主义运动最杰出的诗人之一,他也被公认为是其后的超现实主义的鼻祖。二战后诞生于美国的“垮掉的一代”的诗风也深受兰波影响。今日人们在追忆现代诗歌的发展历程时,兰波的名字都是绝对不会忽略的。就连恐怖小说作家托马斯·里戈蒂也曾在不同场合表示自己是兰波的忠实追随者。